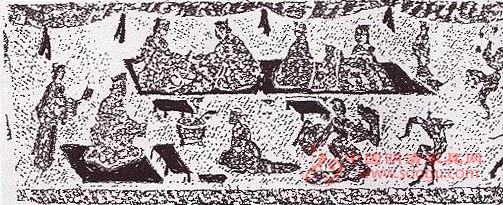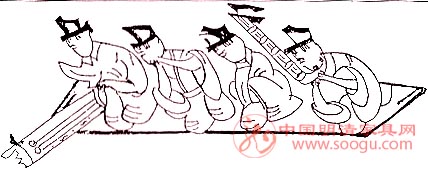|
布席、登席以及席的使用均有严格的规定,《周礼.春官》中贾疏曰:“凡敷席之法,初在地者一重即谓之筵,重在上者即谓之席。”
登席必须由下而升,并且后入室者不得蹋先入者的履,也不得践踏坐席。这就是《礼记.曲礼》中所说的:“毋贱履,毋踖席”。否则就是违反了礼法。在席的使用上还有单席与连席之分,有对席与专席之别。
单席——单席是为尊者所设。《仪礼.乡饮酒礼》有“众宾之席皆不属焉”。不属就是不连,人宾皆是单席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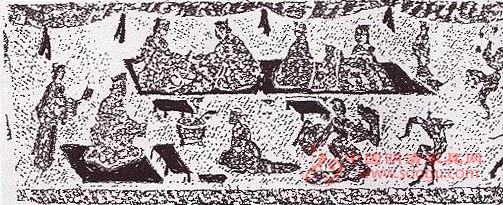
图16
图16是四川成都东汉墓出土的画像砖。
连席——连席是群居之法。古时地敷横席可容四人,此时当推长者居于席端,如果有五人,则要推长者坐在另外的席子上。《仪礼.公食大夫礼》中有“司宫具几,与蒲筵常,布纯,加席寻,玄帛纯”。常与寻都是古代的度量单位,八尺为寻,被寻为常,即一丈六尺。下铺一丈六尺的蒲席,上加八尺的席,可能就是群居之连席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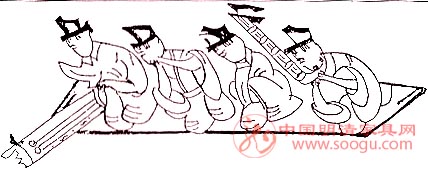
图17
图17是山东沂南汉墓出土的画像砖
对席——《礼记.曲礼》有“若非饮食之客,则布席,席间函丈”。非饮之客就是来讲问之客,此时布席则要布相对之席,以便互相讲问,而且两席之间还要距离一杖之地,“以便指画”。在《仪礼.少牢馈食礼》中也有“司宫设对席”之法。

图18
图18是四川成都出土的汉画像砖。
另外,《礼记.曲礼》中还有:“有忧者侧席而坐”,所谓有忧者就是亲有病,此时则要用特别的席子。“有丧者专席而坐”,这是说有亲丧则要坐单独的席子。其次还有“加席”和“重席”的礼法,都是对尊者的礼貌,要视身份、地位的不同而定。
(二)设席的多寡见等级,布席的种类示尊卑
等级、名分、尊卑、次序,不容紊乱与违反是奴隶制时代的核心思想。所以在席的使用上也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。《周礼》说:“天子之席三重,诸侯二重。”《周礼.春官》有“大朝觐、大飨射,凡封国、命诸侯,王位设黼依,依前南乡,设莞筵分纯,加缫席画纯,加次席黼纯,左右玉几”。纯是席的边缘,莞筵纷纯就是莞席的白绣为边;缫席画纯就是缫席以画五色云气为边;次席黼纯就是竹席镶黑白相间的花纹为边。两君相见或天子时祭都是这三重席,这是最高等级,是为天子所设之席。
诸侯是两重席,“蒲筵缋纯,加莞席纷纯”。缋同绘,也就是“对方为次画于缯帛之上与席为缘也”。
天子待诸侯“莞筵纷纯,加缫席画纯”。
天子待诸侯卿大夫则布群居之席,“蒲筵常、缁布纯,加萑席寻、玄帛纯”。
天子若宴自己的臣、孤、卿中的上等之人,则设单席而不设群居之席。
在《周礼.春宫》中对于祭祀之礼,郑玄说:“天子大袷祭五重,谛祭四重,时祭三重”,而“诸侯袷祭三重,谛祭二重,时祭亦二重”。“卿大夫以下惟见一重”。袷祭和祭都是古代天子、诸侯的祭礼,集合祖先神位于太庙的合祭。总的说,席的使用是以多重为贵,敷席时,以粗席在下,细席在上,即谓“下莞上簟,乃安斯寝”。当然也有特别的情形,那就是天子祭天时则用“蒲越藳”,是去的禾杆所编的草席,是一种粗席。这是古代天子祭天时以表示反本修古之意。《春秋左传.桓公》中有:“大路越席”与此义同。大路是天子祭天时乘的车,越席就是蒲席。郊祭时用粗席,即是《礼记.礼器》中所说的“礼也者反本修古。不忘其初者也。......莞簟之安,而藳之设”。
在丧礼之中,席的使用也有尊卑之别。《礼记.丧大记》说:“小敛于户内,大敛于阼,君以簟席,大夫以蒲席,士以苇席。”就是说,国君死后的小敛、大敛是用教细的竹席,大夫用蒲席,士则用较粗的确苇席了。
正因为席的使用尊卑有序不可僭越,所以《礼记.檀弓》中记述了曾子临死前坚持守礼换席的故事:“曾子寝疾,病。乐正子春坐于床下,曾元、曾申坐于足。童子隅坐而执烛。
童子曰:‘华而睆,大夫之与?’子春曰:‘止!’曾子闻之,然曰:‘呼!’曰:‘华而,大夫之箦与?’曾子曰:‘然。斯季孙之赐也,我未之能易也。元起易箦!’曾元曰:‘夫子之病革矣,不可以变。幸而至于旦,请敬易之。’曾子曰:‘尔之爱我也不如彼。君子之爱人也亦德,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。吾何求哉?吾得正而毙焉,斯已矣!’
举扶而易之。反席未安而没。”
在这里记述了曾子严守礼制的故事,他知道自己不是大夫,不应使用华美的竹席,所以他批评他的儿子和弟子不叫换席是见识短浅的“细人”,坚持换掉不合于他身份和地位的席子,以至“反席未安而没”了。
《尚书.周书.顾命》中也记载了布席的故事:周成王死后,仍为他四坐布席,如他生前一样,以显示其天子的权力与地位。
“间南向,敷重蔑席、黼纯”;
“西序东向,敷重底席、缀纯”;
“东序西向,敷重丰席、画纯”;
“西夹南向,敷重荀席、玄纷纯”。
席所代表的权力和地位,以上种种可见一斑。
(三)燕居布席中的长幼尊卑
《礼记.祭义》中有:“七十杖于朝,君问则席。”即是古代允许七十岁老人拄杖上朝,若天子有问,则布席与天子合作。
《礼记.曲礼》中详细地规定了晚辈为长辈奉席之法。如:“为人子者,居不中奥,坐不中席。”在古代,若四人之席,则席端为上,若单席则席中为尊,为人子者不可坐于席中。
又如:“奉席如桥衡,请席何乡,请衽何趾”就是说敷席时如桥衡,左高右低,要随长者的意愿,奉坐席要问朝什么方向,奉卧席时则要问足朝什么方向。
《礼记.内则》又云:“父母舅姑将坐,奉席请何乡,将衽,长者奉席请何趾。少者......敛席与簟.......敛簟而之。”(,藏也)“父母舅姑之衣、衾、簟、席、枕、几不传。”(不传就是不敢转移他处)又云:“夫不在,敛枕箧簟席,器而藏之。”这是规定为人子者,不敢动长者席子;为人妇者,若夫不在,妻子还要将丈夫的席子收藏起来。
由以上三礼中所记载的布席、用席之法,虽如此繁冗庞杂,但离不开一个中心思想,那就是等级分明,尊卑有序。
席,在奴隶制时代,既是起居的必需坐具,又以不同材质、不同边饰和不同的使用规则,来体现不同身份、不同地位和权力,它是周朝政治制度的一部分。
另外,筵(与席通)还是周代建筑面积的计算单位。如《周礼.冬官.考工记》有:“周人明堂,设九尺之筵,南北七筵,堂崇一筵,五室,凡室二筵。”“室中度以几,堂上度以筵,宫中度以寻,野度以步,涂度以轨。”贾公彦在注疏中补充说,“夏度以步,殷度以寻,周度以筵。”说明周朝乃是以九尺之筵为建筑的计算单位。 |